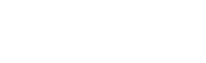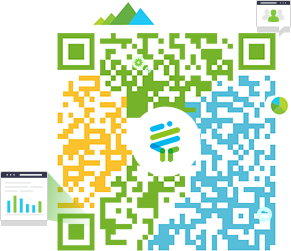导语:
苏文清 刘晶
提到中国的成长小说,就不能不提北京大学的曹文轩教授。理论上,曹文轩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西方成长小说的概念,提出了中国成长小说的命名问题,并对成长小说的内涵与外延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促进了成长小说的青春抒写转向;实践上,曹文轩创作了被称为成长三部曲的《草房子》《红瓦》和《根鸟》三部成长小说,对中国成长小说在主题和艺术形式的创新上具有示范作用,对中国儿童文学向青少年文学的拓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概念的新变:青少年文学的代名词
曹文轩将中国成长小说的“成长”指向“高年级以上、成人以下这一段”[1](139),将成长小说所叙述的内容界定为对成长本身的解读,包括成长过程的神秘感、恐怖感、痛苦感等,直至化蛹为蝶、破壳而成“新人”。
这样一种界定在儿童文学界引起了共鸣。梅子涵等人也认为,成长小说的“成长”指的是儿童“往成人跨越的时候突飞猛进的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是儿童往成人跨越的时候出现的一些故事和心理变化”。[2]
然而这种界定将成长小说与青少年文学等同,是曹文轩等人对中国儿童文学多样化发展可能性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与欧美的成长小说观是不同的。成长小说一词虽然来源于西方,在西方的认识也并不统一。但美国理论家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的观点基本可以代表西方成长小说的核心思想:“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3]从M. H.艾布拉姆斯的定义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将成长小说成长的时间界定为“从幼年开始”,而中国学者却把成长的时间确定在青春期。所以在梳理成长小说的西方渊源及中国衍变时,有学者将在中国的这种衍变称为“青春主题”抒写。[4]
那么,中国的成长小说为什么会衍变为“青春主题”的抒写呢?主要是因为中国青少年文学长期处于缺失状态,既有的儿童文学创作体系无法表达青少年成长的主题,而致力于抒写青少年生活的创作又常常招致“成人化”的批评。于是青少年文学成了“成人文学不管,儿童文学想管又无力管” [1](138)的领域,曹文轩于是将西方的成长小说的概念拿来指称这“成人文学不管,儿童文学想管又无力管”的所谓“两不管”的文学,以吻合青少年生理、心理急剧“成长”之意。
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来说,曹文轩成长小说概念的引入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打破了儿童文学单一的审美格局,在理论上将儿童文学区分为幼儿、童年、少年三大层次之后,对青少年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作出了具体的探索,使成长小说有可能成为青少年文学中的重要题材,从而为青少年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其次,打破了传统儿童文学在题材、主题方面的限制,将中学生早恋、父母离异、社会某些方面的阴暗面等纳入儿童文学的表现范围,扩大了儿童文学的题材范围,提升了儿童文学对生活的表现能力。
最后,为长期背着“成人化写作”黑锅的青少年文学创作者正名,肯定他们在题材开拓与审美表现方面的开创性意义。
然而,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在成长小说的旗帜下迷恋于少年青春期独有的生理变化的描写,使成长小说几至于成为青春期文学的代名词,这也并非成长小说倡导者的初衷。那么,中国的成长小说对传统儿童文学的主题与艺术表现形式存在多大的突破空间呢?曹文轩的成长三部曲《草房子》《红瓦》和《根鸟》作了可贵的探索,具有极强的示范意义。
二、主题的突围:苦难、丑恶与刚毅
由于旧有的儿童文学创作将读者群体对准低幼与中高年级学生,它要求儿童文学作家向读者展示一个纯净、美好的世界,因此作家在展示世界时必须有所讲究、有所选择,甚至有所遮掩。所以儿童文学实际上不得不做“隐瞒”的事情。曹文轩认为“这种‘隐瞒’不能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因为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了,此时想瞒也瞒不住了。如果说从前的 ‘隐瞒’是合理的,那么现在的‘隐瞒’就离欺骗不远了;如果说从前的‘隐瞒’是有利于他们成长的,那么现在的‘隐瞒’对他们的成长恰恰是不利的。它将越来越成为一个道德问题。”[1] (143)
将是否对读者“隐瞒”现实生活中不纯净、不美好的一面上升为道德的高度来论述,表明了曹文轩突围旧有儿童文学主题的决心。因而,曹文轩在自己的成长小说中执着于表现成长过程中的苦难与挫折,揭示社会的丑陋与丑恶现象,努力塑造饱受风雨挫折之苦的小小男子汉形象。
(一)苦难与挫折
曹文轩认为,成长是一个充满痛苦的过程,[1](40)因而在苦难与挫折中获得成长是曹文轩作品主人公的共性。如红门里家道中落的杜小康(《草房子》),家庭的巨变使他过早地承担了男人的责任。但与父亲一起野外放鸭的那段时间,他经受住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考验——与孤独寂寞的较量。刻骨铭心的孤独痛苦之后得到的解脱,使少年的杜小康多了一份男人的自信,即使后 来在油麻地小学门口摆地摊,他也是从容的,正如桑校长所说的那样,“以后可能就算他最有出息了”。
桑桑(《草房子》)成长于“死亡”之后的“新生”。表面上看桑桑的成长完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实际上,当鼠疫中的桑桑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个节目——带柳柳看城墙后,他的成长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称得上是真正的男子汉了。
根鸟(《根鸟》)的旅程更是一次布满了苦难与挫折的征途。就像苦难与挫折的磨炼给了杜小康自信以及自力更生的能力,给了桑桑对人生对生活的顿悟一样,苦难与挫折也给了根鸟一个男人不懈追求的气概和能伸能屈的韧性,给了秃鹤在赢得同学们的尊敬时的眼泪。
曹文轩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表现成长中的挫折并不仅限于学习上的压力或者生活奢侈侈品的匮乏,而是将笔触对准青少年人生路上的经历,他们的苦难来于心灵的煎熬和灵魂的拷问。挫折、苦难之后并非简单地使父母高兴,让社会满意,而是对人生多了一份感悟,对肩上的责任多了一份承担。
(二)丑恶与恐怖
虽然曹文轩是一个非常唯美的作家,但为了表现青少年生活的真实状态, 他并不遮蔽丑恶与恐怖的一面。他认为:“面对丑恶,面对真实,这是成长小说区别一般儿童文学的地方,在将社会向主人公公开方面,成长小说可能要比一般儿童文学少许多禁忌。他们要经历重压,承受一般儿童文学所无法承受的东西。”[2]只有当作为主人公的孩子们发现了这些丑恶的、真实的禁忌,他们才能获得心理的成长,得到真正的成熟。
在《红瓦》中,曹文轩就写到了少年对成人世界丑陋一面的窥探,既包括成人生活中丑陋的一面,也包括政治斗争中人性的丑陋。
丑恶的社会现实是让成长中的少年感到恐怖的,除此以外,曹文轩的主人公还要经历更多的恐怖。根鸟旅途中的恐怖是不言而喻的:被骗到鬼谷里的根鸟每天开采矿山,还要受毒打,那些人甚至还用毒品来控制这些苦力们的精神,让他们不能逃跑。还有旅途中的人情冷暖,都是根鸟未曾想过的。丑陋的、可怕的并不是肉体上的毒打,而是精神上的虐待。
(三)刚毅与坚韧
曹文轩在表现苦难、挫折、丑恶与恐怖的同时,也表现了应对这些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刚毅与坚韧。只有刚毅与坚韧的青少年才能战胜挫折与恐怖,获得成长。
曹文轩常常用超出少年承受的苦难去历练他的小主人公。《根鸟》的主人公根鸟所受的苦难自不必说,父母在沉船事件中丧生的少年阿雏(《阿雏》)、与瞎眼奶奶相依为命的少年(《海牛》)、父母早亡认柳树为妈妈的秀秀(《充满灵性》)、母亲偷情父亲自杀的少女(《蔷薇谷》)、背负“偷 船”罪名的何九(《田螺》)……他们都在各自的故事中承受着生活的巨大磨难,并最终战胜了苦难,迈向成熟。他们战胜苦难的途径也许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精神品质、意志却同样的刚毅与坚韧。正是在这里,我们理解了曹文轩表现苦难的意义:向成长于当下的青少年传授战胜困难的法宝——刚毅与坚韧。
曹文轩认为创作儿童文学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塑造“精明强干”的未来民族的接班人,而不是为了给儿童以“乐趣”。“当代的儿童文学应该对那种顺从的、老实的、单纯的儿童形象加以否定,塑造坚韧的、精明的、雄辩的儿童形象。它应该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族是开朗的、充满生气的、强悍的、浑身透着灵气和英气的形象”[5]。
当儿童的世界向成人拓宽后,儿童的视野也会更加辽阔,表现儿童生活的艺术手法也会进一步拓展。
三、表达的拓展:神秘与空缺
对神秘现象的展示是旧有儿童文学所不提倡的,因为对神秘现象的不可解释而带来的恐怖情绪被认为是影响儿童心理健康成长的。但曹文轩深知“成长充满了神秘感”[1](139),所以他的成长小说大胆渲染一种神秘气氛。
他的作品里有很多神秘人物。他们有的来历不明,如《红瓦》中的乔桉;有的去向不明,如《草房子》中的纸月;有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以两个断点的形式出现,中间一段经历神秘莫测。有的根本就不是现实存在的人,只出现在其他人物的回忆、对话或者梦中,如《根鸟》中的紫烟,她的呼唤,是根鸟开始这段人生旅程的缘由,也是不断激励着根鸟前行的动力,但她仿佛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根本就不现身。
为了渲染这些神秘人物给作品带来的神秘形态,曹文轩采用了 “空缺”化的叙事策略与少年儿童的主观化叙事视角。
“空缺”化的叙事策略来源于1936年阿根廷文论家博尔赫斯的“无限性叙事”
模式,可以使故事无限地延伸下去,他为世人提供了小说的一种独特的结构——开放性结构:它包括开头缺失,结局的不可达,结尾缺失,多重结尾,过程化文本以及注释、间断、累赘手法的使用等多种形态。[6]这种叙事可以在关键的情节上留出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想象,有的甚至在以往最为重视的结局故意空缺,挑战读者的阅读定式。
赫尔博斯的“空缺”化叙事模式受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作家的追捧。先锋文学以反叛性和实验性而著称。除了在内容上颠覆故事、解构意义,他们最热衷的就是文体形式实验。而“在文体实验中,格非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是使用有意识的省略,让事件的关键环节缺席,从而造成叙事上的空白和断裂,给文本的意义留下多元解释的空间。”[7]
曹文轩对格非的“空缺”化叙事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中谈到了格非“空缺”化叙事的实质。跟随着格非的脚步,曹文轩也开始了他的叙事实验。比格非走得更远的是,他将这种叙事用到了儿童文学领域,用到了当时还在命名过程中的成长小说的创作实践。
用“空缺”来制造神秘,绝对是一个百试不爽的手法,未知的人和事物总是叫人提心吊胆,但人的好奇心又是无时不在的,尤其是少年儿童。为什么曹文轩的人物常常神秘莫测?那是因为在关于他们的叙事中经常出现信息空缺,或者背景空缺,或者去向空缺,或者经历空缺,再或者是人的肉体的空缺。来来往往的陌生人,从陌生到熟悉;生活的突变,从优越的少爷变为自力更生的小贩;寻梦途中的曲曲折折,永不放弃……一切来得莫名其妙,神秘就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中反复出现。“空缺”,在时间和空间上为神秘主义的出场制造了绝美的舞台。
“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现实世界,同时又淡化这个现实世界的时代性、真实性,往往会给读者一种在现实世界和神秘世界彷徨迷离的审美感受,而在现实与幻想交合的世界里,读者更易关注故事传达的寓意,而不是故事本身,大概这便是作者这样处理小说的奥妙。”[8]
如果说格非的“空缺”来自于他小说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的不同步,那么曹文轩的“空缺”,则与他特定的叙事视角密切相关。
曹文轩的小说基本上都是采用主观化叙事,用一个主人公穿起一连串独立的小故事。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学校的生活,追寻的梦想,这是桑桑、林冰、根鸟们的生活和他们的世界。杜小康的失学游荡,在桑桑们看来,是很值得羡慕的事情。复杂的政治斗争,在林冰们的眼中,只是几个人的交替上台。而一段充满了艰险与诱惑的旅程,于根鸟们而言,只是为了解救一个叫作紫烟的女孩。断裂的事件,简单的视角,模糊了人性的恶与丑,让真善美渐渐凸显。这就是曹文轩运用“空缺”化叙事从儿童认知方式来阐释的纯美世界。而这正是曹文轩主观化叙事的独特之处:少年儿童的主观化叙事。
儿童认识这个世界,一般是以自己为中心参照点,来观察这个社会的。由于认知的局限性,他们会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事情,这样就容易形成由认知带来的叙事空缺。由于接触生活面的局限性,他们在了解信息方面也不如成人,所以这也会形成由信息空缺带来的叙事空缺。这样就形成了如下的良性循环:因认知和信息的空缺而形成神秘感,因神秘而探寻,因探寻而展开情节、在情节的发展中补充认知与信息,获得成长。
儿童视角与“空缺”化叙事近乎完美的融合使曹文轩在成长小说的探寻与文体实验方面获得了双丰收。这一成功的意义非同寻常。首先,它证明外来叙事理论同样适应于中国文学,这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接轨提供了借鉴。其次,它证明文体实验同样可以在儿童文学领域展开,这为拓宽儿童文学的艺术表现领域探明了道路。最后,它证明中国式的成长小说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方面都可以与低幼文学与童年文学拉开足够大的距离,这为成长小说的发展竖立了标杆。
四、小结
与国外的成长小说相比,曹文轩在时间上把婴幼儿时期、童年前期排除在成长小说的表现范围之外。他既不像德国成长小说那样刻意强调少年的成长必须向社会生成,也不像美国成长小说那样突出少年对社会的抱怨与批判,曹文轩的成长小说专注的是少年意志品质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未来性格的形成。他让少年在苦难中发现神秘,在战胜挫折、揭示神秘中形成刚毅与坚韧的性格,从而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他们的成长就是发现与揭示秘密的过程,发现了,顿悟了,就获得了成长。
曹文轩用他的探索告诉我们,中国的成长小说在内容上可以打破传统儿童文学在题材、主题方面的限制,可以将一些丑陋的、恐怖的、可怕的但又真实的事情纳入儿童文学的表现范围,诸如家道中落、辍学、失踪、偷窃、杀人、偷情、乱伦、社会动荡等都可以有所涉及。形式上,成人文学的传统与先锋的表达方式尽可以拿来,但必须与少年儿童的接受能力相匹配,不可过度拔高与降低少儿的审美接受能力。相对于传统的少儿文学,不局限于性的内容的突破与不局限于传统表达方式的形式的突破,是曹文轩为我们探索的中国成长小说的特质。
原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8卷第2期
参考文献
[1] 曹文轩.论“成长小说”[C]//赵郁秀,当代儿童文学的精神指向——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文选,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
[2]梅子涵,曹文轩,方卫平等.中国儿童文学5人谈[M].天津:新蕾出版社,2001:145.
[3] [美]M. 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18.
[4]徐秀明,葛红兵.成长小说的西方渊源与中国衍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1):82-93.
[5]曹文轩.曹文轩儿童文学论集[C].南昌:21世纪出版社,1998:112.
[6]王钦峰.后现代主义小说论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49.
[7] 王爱松.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57.
[8] 李芳.论曹文轩成长小说的象征艺术[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1 ) :300.
热门文章
中国台湾地区宣布6月30日前关停3G服务,闲置频段将投入5G发展
2024/4/1 17:12:02弗若斯特沙利文:百度文心一言稳居国产大模型第一
2024/3/27 14:26:11网飞版《三体》今日开播:刘慈欣担任顾问
2024/3/21 20:00:21小米汽车SU7/Pro/Max正式发布并上市,21.59万元起
2024/3/29 10:40:35特斯拉大裁员殃及上海厂,电动车该泼冷水了
2024/4/16 14:37:02艾瑞观点 | AIGC技术在营销领域应用三大方向
2024/3/29 10:27:22

扫一扫,或长按识别二维码
关注艾瑞网官方微信公众号